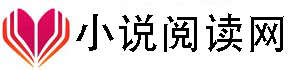22-30(15/51)
怎么到这会子才发兵平乱?”“官家的事,谁晓得。”宗契道。
不过横当眼前的不是瞧热闹,而先是填肚子,再是想个出路。
两人便找个食店,叫下几碟子冷热茶饭。宗契间隙问她:“你可有投奔之所?”
这话他从前问过。那时应怜神魂无措,只顾自伤,以为全天下人都弃她唾她,哪有什么投奔;然经历这么些事,现在想来,是否也太过绝对。
雕花匣里,她还存着簪钗银钱,与赠她的那首诗;
宗契见她专捡那桌上姜辣羹、芥辣虾两样辣食下筷,不由得笑,“原来你爱吃辣。”
她咬下一口鲜鲜辣辣的虾肉,想着心事,望定他,便也有了些笑模样。
正有堂中乐妓,挨向一桌后生打酒坐,琵琶半面,轻启朱唇,唱的是唐时徐侍郎诗,道那“天下三分明月夜,二分无赖是扬州”,词清韵妙,引得子弟赏赐调笑。
应怜
被勾动了心思,停下箸,细细听了一晌,别有一般不与人言的滋味叠叠漫漫,涌上心头。
琵琶歌毕,乐妓谢了赏,自去了。末了,应怜开口,“我有了一个去处。”
宗契点头,“哪儿?”
“我有一个表姐,自幼一处长大的。”她慢慢想来,有几分回忆的光景,“四年前,她随父回了祖籍,就在扬州。”
宗契却听出点话外之意,“如此说来,你们四年未见了?书信可一直通么?”
应怜摇摇头。
“人不来往,书信也不通,你知她现下如何了?”他皱眉,觉得不妥,“况人心易变,想她未必肯留你。”
心中则想的是,不若还跟他回代州,搁在眼皮子底下,他也能放心。
“她……她不一样的。”应怜怔了一会,方道。
有些事,她得闷在肚里,哪怕是对宗契,也不能言讲。
“我们临别时,她曾对我讲,今后不论山高水长,起起落落,一定去找她。”她道,“如果情谊还在,她必会留我。”
她既这么说,宗契也不好驳,点头道:“成,那便去试试。你那表姐,她叫什么?”
“——定娘。她叫李定娘。”
定娘比她大四岁。
因连着她年幼丧母,应怜的娘亲张氏便时常接她家来小住。据张氏回忆,那时应怜还未出,家中只应栖一个浑小子,故与其说定娘是内甥女,莫若说是半个女儿。
自有记忆来,应怜便跟在定娘身后习惯了的。定娘说往东,她绝不往西;定娘让打狗,她绝不辇鸡。
定娘对她也好,但凡雅集游宴,别的女娘都不敢对她有一二分捉弄,已是被定娘叫骂怕了的。故应怜一直以来这么个犹犹豫豫的性子,不致招惹别人欺负。
她喜爱定娘,就如自己有了个亲姐姐。
只若不是那次风波,定娘想必还留在洛京,她们也不致南北相隔。
如今四年未见,音讯不通,也不知她嫁了没。还是就像那回分别时,她一边哭一边说的,“我不要再嫁人,以后老死在家中便了。”
几年来,定娘一直是她一块心病。
想到此处,应怜又有些怅惘,既不知她如今过得怎样,也不知她会不会怨自己。
不过计议已定,她到底还有几分雀跃,与宗契一道,定了行程。
平江府距离扬州路程不算短,最稳当的去法便是走水路,沿漕河船行一路往北,虽入冬北行不顺风,但也比陆路马车颠簸来得舒服。
如今有了银钱傍身,各处都宽便。应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