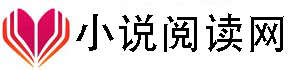120-130(12/32)
有几件事,在浩繁冗杂的布置事宜中,像沧海里几粒粟米,不经意便划过了。一件便是郭显本人自请随单铮北上,理由无可厚非,只因他是郑武陵的表弟,若想说动郑武陵调集边军,非他出面不可;由此,赵芳庭重新做了一些部署,以护保郭显为由,又多添了些自家心腹战将。
另一件是吴览身边的一名小厮袁武,独自来见单铮。单铮打心眼里厌恶匈奴人,只为着他曾于吴氏有恩,才留他在宁德军,一向只眼不见心不烦。没想这一回他却自个儿找来,头一句开口便是:“我本不叫袁武,是乌孙小昆莫部蒲察贵主之子。我仰慕将军的为人,故今日请行,回到乌孙,一则与家人团聚,二则可时时关注部族,若有异动,便提早报与将军。”
单铮神情冷峻,极锐利地扫量了他一番,问:“你是匈奴人,为何反帮着异族?”
袁武身形高挺,兼有初具的锋芒与深邃的俊美,随着二年来长成,面貌与中原愈发迥异,“我不独为中原,更是为己。若与中原讲和,以草原的牛羊换取你们的米粮布匹,用不着流血便能养活我们的妇人与孩子,这是我乌孙的百姓都乐意见的。我若促成了讲和,必受子民拥戴,归蒲察氏后便能立稳脚跟。”
“边关曾也设榷场交易,可你们还不是背弃盟约、烧杀抢虏?”单铮十分冷淡。
“邻人之间尚且有争斗,国与国又怎会有永不背弃的盟约?”袁武并不慌张,仍道,“且不论从前的榷场中,中原商人怎样欺骗诡诈,至少战争对双方都无好处。我愿榷场再开,并承诺有朝一日,若能为主,必约束子民,再不发争端。”
对此,单铮给出回答:“你是吴先生的随人,去留与否,无需我首肯。我不扣你,你只与他求情便是。”
袁武立直了身子,低头攒手,郑重行了个乌孙的礼,而后离开。
选调精兵、集结粮草仅花费了一日夜。一切俱备后,单铮率一万兵士自江宁南门而出,趁着月晦星淡,人衔草、马衔枚,几乎是悄无声息出离了江宁。
不过前后脚功夫,翌日天明,离江宁州城二十里上游处,江面之上,自西而来了一支浩无边际的战船队列,大如飞虎、小如海鳅,上列战旗飒飒,映日的盔甲连片成行,森然罗列。
随着一声警醒御敌的战鼓沉雷般轰鸣,宁德军战舰倾出,汤汤江面之上,就此展开水战。战船之间厮杀无数,击沉船只亦无数。碎橹残骸、尸首断躯源源不断自上游漂下,鲜血随浪翻滚,染得滔滔江水成了翻滚的赤色波涛。
宗契率兵从天晓直杀到日入黄沙,终于闻得对面鸣金而退,才摆阵回师;点集兵马,伤损了二千余,估摸着对面死伤数倍于自己,勉强算得上退敌大捷。
然攻守之势未变,且据斥候传来的战报,后方官兵陆续集结,到如今已有数十万众,夜间连营灯火彻地连天,几乎照得黑夜通亮,彷如日坠于野。
渡江强攻未必能取胜,可随着时间推移,更远处上游早已渡河的官兵终于自江南面而来,发起了陆路的进攻。
情势之急,犹如千斤悬丝,每一时辰,都有派出的斥候回报,告知敌情。吴览迁江宁城外百姓入城,拆毁城外房屋、坚壁清野。城中百姓惶惶,不分昼夜,常听震鼓浑浑,无数兵士列阵飞驰。
好在此时节,旱地逢甘霖,沂州的援兵二万,由陶慨领着,自东北渡江而来,终于入了江宁。
陶慨仍是那样豪壮的性子,甫入了城,在急来迎接的将领当中,便问起单铮与宗契;吴览多日未曾阖眼,一身衣衫皱褶、胡子拉碴地出迎,详细说了一遍分兵取洛京的计策,又道:“军情急迫,无暇召回部将,为将军接风;待来日江宁之围解后,再谢将军义气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