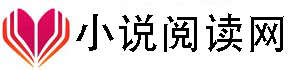120-130(1/32)
第121章 第121章絮果飘摇沉复起,向日……不是子承父业,却是兄终弟及。转过一年,堪堪开春之时,三辞三让的戏码匆匆过完一遍,三王正坐大宝,登基为帝。
此一年为继隆二年。因三王即位,来路不正,欲要大显人主之能,又想掩人耳目,因此在元羲的谏言下,将改元之事暂缓一年,也免得祭天祭庙又闹得兴师动众。
新帝甫一登基,急待把稳手中权柄,又想做些万民称颂的事,寻来寻去,眼光便盯上了江宁。
先帝在位时,朝堂羸弱,不欲与江宁起战事,固上下皆有睁一目眇一目、与宁德军相和之意,久未发兵攻打。轮到新帝,便有些意动,不愿见宁德军再坐大,想要除之而后快。
然到底根基尚未稳,得位又有些不正,因此上便瞻前顾后起来,索性开了一回朝议,专讲那宁德军之事。
若论本心,新帝郭禧是想打的,且自负一身刀马弓矢之能,恨不得御驾亲征,剪灭叛匪,与朝臣们言语之间,便点出了三分意来。
没料想以几位三朝的老臣为首,不接这话茬,反倒提起去岁秋冬匈奴犯边的事来,说镇军大将军郑武陵又多求粮草军饷。郭禧好一阵闷闷不乐,却又不好发恼,只因那郑将军是元慈太后的母家人、先帝的表兄,拥重兵于边疆;先帝不明不白殡天,若他当真不依不饶,恐怕郭禧也坐不稳这龙庭。
“大将军屯兵戍边,本是劳苦功高,便多发些粮草军饷,也是应当。”郭禧捏着鼻子认了这么个讹诈事,又不理那几位老臣,目光放远,再问,“江宁匪祸日甚,万民以此为苦,何如?”
又有臣子来谏,道是度支不足。气得郭禧御案下拳头捏得咯吱吱响,差点骂出声来。
此时终有人出列上奏,正是新近才升任大理寺少卿的元羲。郭禧本也要点他的名,见他出班言语了,胸中一口闷气便散了一半。
元羲果然明晓帝意,力主一战,且给出的理由无可辩驳。
“昔春秋时,三家分晋,本害正统,当为诸侯所攻灭;然前周室天子羸弱,竟坐视其大,且允其裂土,三家由是正名,诸侯再无攻伐之理。礼崩乐坏自此始。今我朝比之周室,地愈广而国愈盛;彼贼人仅踞一城,远逊韩、赵、魏三家列卿。剿绝之势,如箭在弦上。不然,如其效三家之不义,而我大周竟拱手壁视;当剿时不剿,欲剿时已而不能,岂不学前周之自取灭亡?”
首列几个老臣仍欲辩奏。郭禧却点头,望向一边心腹的武将,便有亲信将首出班附议,言辞凿凿。郭禧听罢主战之言,胸臆长舒,竟不再给余臣说话的机会,起身罢朝。
私下里又留了元羲说话,只在资政殿的小书房里,以示与臣子的亲近。
元羲主战,还有个不得不如此的理由,只是朝堂之前不好明说。此时君臣二人相对,他便将话无所保留地讲了出来。
“官家得位,虽问心无愧,然终有人不服,究其根本,是因兵权未稳。江宁需攻伐,官家也急需如此一役,待贼匪诛尽,将士齐心,官家可将兵权尽掌于手,到时便再无人有二心。”
一语正中郭禧隐秘之处。
郭禧颔首,连声道:“墨池甚得朕心,可为股肱!只是边疆乃朕的心腹隐患。郑将军是先帝的戚党,恐怕难为朕所用……”
“郑将军是个粗豪忠正的武夫。”元羲宽解上意,“他如今要粮草,正是不知官家如何发落他、为着试探帝心之故。官家只当厚恤他军民,粮草辎重较以往更丰,以示安抚,他今后必以您马首是瞻。”
郭禧觉着十分有理,心中又对元羲倚重了三分,不觉面上漾出了笑意。
以往便知他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