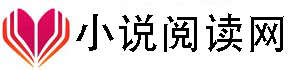110-120(5/34)
的苇子,好不好?”她放轻柔声音,又问。这一下那孩儿眼睛亮了,点点头,露出个笑,又有些害羞,把苇箔卷了,踮起脚往应怜怀里一塞,生怕她反悔不要。
应怜把鱼、钱与酒米一齐换给了她,她便一溜烟跑去后头了。
没待屋主人再出来,应怜同宗契携着编了大半的苇箔,慢慢地向村店去。
她心里头想得杂乱,无非是这家的男人约摸也像邻人,不是走了就是死了;又想到那些人或许被征了为官府做活,像年前被征去固堤的人那样,堤毁了,人也就冲走了;或他们此时就在江宁、在宁德军中,也不过是妻离子散。
便又想到,不知往后哪一年,宁德军打去洛京,也要行径此处,到那时这一家母女是否要罹难,或在那之前就已走了或死了,就连她将要去的挂了酒旗的村店,也不知那时是否还能留存下来。
这些注定没有答案的疑问太过沉重,连这几日的欢乐,一并都从她心中抹去了。
直到宗契出声,打断了她愈发消沉的想象,“只是可惜,再没沾了芥酱的炙鱼了,嗯?”
应怜思绪一断,心神被拉扯回来,偏头望着面含微笑的宗契,他英朗的眉眼浸在柔和温暖的午日光亮里,那一份眼角眉梢的锋利与棱角在她怔然的目光下,连安慰也变得和缓无声起来。
她勉强笑了笑,又觉得难为情,“有人终日冻饥,我却还为芥酱或蜂蜜争执。”
宗契叹了一声,那叹息中也有隐约的笑意。
他一只大手蒲扇般盖上了她头顶,将阳光遮去,也将她钻牛角尖的劲儿遮了,轻轻抚了抚她头发,片刻才开口:
“这世上人本就多。有人贫、有人富、有人饱、有人饥,你有饭可食、有衣可穿、有屋可避风雨,这是你的福运;而没有得到这些的人,他们固然可怜,却不是你的罪过。有多少人只是在心里悯弱怜贫,实际上却连一个子儿都没施舍过。你能见贫弱而施援手,已是很好的善举。若你行了善事还仍羞愧,那么天下未行善事的人岂不得掩面自尽?”
应怜默默听着,他话声不大,却如浸润山林的酥雨,一点点渗进她心中,使她心中的焦渴得以减轻,那股不知由来的愤懑也一丝一丝被抚平。
但毕竟还有些怅然若失,仿佛一叶障目,她只差一点,得以仰见巍巍泰山;只差一点,却心中有毫厘阴翳,就犹如隔了天堑。
“以我只身一人,今日行善、明日行善,哪怕日日行善不绝,一辈子又能善施几人?便如那妇人家,我施予的银钱总有用尽的一天,到那时,她们不还得堕入贫苦么?”
二人在春日中漫漫地并肩走,踏过多少早已无人迹的野草荒郊。应怜将心中磐固不去的失意缓缓道出,不奢求他能指出一个确切的答案,只是纯粹地与他分享心底里的烦恼;又想起苦难并非只源于贫困,如自己、如定娘,甚至如那个生在天底下最尊荣、最威赫的富贵窝里的六皇子郭显。
“贫困时因贫困而悲苦,富贵时又因富贵而生出种种恐惧。”她琢磨自己的心意,试着将心中所想用言语吐露,“难道为人的一生,总有数不尽的烦恼?先前我因不忍见那对母女贫苦而施舍银钱,按理说施舍后应该快意满足,可却因此又生了更多的忧思——只因愿天下人皆衣食有着,却也明了这根本是痴心。若如这般,因有所思有所想而一辈子困在樊笼中,岂非还不如无知无觉的鸟兽鱼虫快活?”
宗契定定瞧她,唇边似有笑,眼却清明如镜,照她所思所想所烦忧所困扰,听她说罢了,静默了片刻,道:“佛中所言人生八苦,你便陷入‘求不得’之中。可正是这样求不得,你才会去求。你愿天下无饥寒,便尽你所能去施善。又所谓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