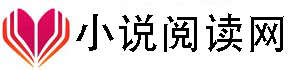22-30(21/51)
逼仄到两人都容不下,附近四野无人,他就不能稍微失礼一点,进来歇息,哪怕找个角落也好呢。她搓了搓发僵的手指,又换了个姿势蜷卧着。
外头似乎听着了她翻来覆去窸窸窣窣的声响,半晌,终于主动来发问:“睡不着?”
“……嗯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那我与你讲则野谈?”
应怜睁开眼,仍是满目的篝火,虽不若先前熊熊,却也还炙热,“你还会讲这个?是哪篇杂记话本?”
“不是什么话本。是我幼时,时常想家睡不着,师父讲与我的。”宗契道。
本就没睡意,这会子她又被勾得兴致勃勃,就着横卧在榻,洗耳恭听。
宗契便说开来,声音不大,恰巧透过门隙,能清晰传入她耳里,像飞瀑击着山石,夜来又多了几分低沉柔和,教她听得入神。
“道是太祖朝广顺二年,有个河东路转运使,姓梅,单名仁,字词实,有一回巡察一路赋税,来到一个偏僻村落,见十室九空,唯有一户人家,种着莼菜,便知定有人居。他入内扣门,道是路过的行人,至此口渴,求一口水喝。
“扣了几下,里头有人答言,却是个妇人,道自家并无男丁,只她独自在家,不便开门留客。梅官人苦求,说一路行了几十里,只逢着这一户,实是口渴,又拿出钱来;那妇人推辞不过,便道:‘官人少待,我戴了盖头出迎便是。’
“不多时,妇人开门,果戴了一青布盖头,四围垂下,教人看不见面貌。梅官人入内,见粗陋冷落,灶上并无米粮,只有刚洗好的两支莼菜,便知这一户贫窘已极。妇人待客甚是有礼数,拿出家中唯一一只碗来,舀了水,捧与那官人;又致歉告罪,道家中无米无盐,无甚招待。梅官人心中不忍,问男丁何在。那妇人道,丈夫早年募去做兵,便再没回来;有两个儿子,大的前几年也被募去了,小的害了疾病,已夭了;去岁阿翁被征去徭役,累死在石场。她自与阿姑相依。没几个月,阿姑也没了,便剩了她独自一人。”
应怜听着觉得心酸,后听得那句“独自一人”,百感交集,闷不做声,咬着唇默默地哭。
宗契还接着讲。
“梅官人心中好生怜悯,见她瘦骨伶仃,一时动了恻隐之心,便取来几张饼,并两块碎银,交与那妇人。妇人千恩万谢。梅官人没了谈兴,喝过水,便出门告辞。妇人送至院口,忽此时,一阵风来,刮起那盖头一角,叫梅官人看了个瓷实。”
应怜吸了吸鼻子,闷闷道:“她必是花容月貌,那梅官人怜之爱之,便将她载上马,一同去了,自此后不必孤苦伶仃,有了依靠。”
外头一时没动静。
半晌,他问:“……那你还听不听?”
“你说。”
“那风吹起妇人盖头,被官人瞧个正着,竟是一颗骷髅,白惨惨的骨殖、黑洞洞的眼眶,那齿间森森,一张一阖,道:‘官人好走!’……”
还未说完,里头尖叫了
一声。
紧跟着窸窸窣窣,约摸是她坐起身来,狼狈地埋怨,“这是什么志怪野谈?谁家大人大晚上给小孩儿讲这个?”
宗契坐定庙门槛,很是自如,丝毫不觉不妥,“我们师兄弟,从小都听这些睡觉。”
应怜满肚子花好月圆,憋得幻梦破灭,白瞎了方才哭一脸泪,愤愤抹了。
“后头还有,你还听么?”他又问。
她哼了一声,“不听了,我睡下了。”
于是闷闷不平地歪倒草铺。
许是这么一悲一吓,她竟真的生了